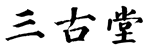那是一個愜意的午後,陽光灑在邊側陽臺上,落下滿目綠溽。
室內,佛龕前香剛焚了一半,一把日本雨宮宗老鐵壺咕嚕咕嚕冒水,茶早就在壺裡醒好,“水簾洞的水仙,先開個味。”
你一邊看著牆上的書畫一邊等茶,不經意低頭,康熙朝的青花杯子,龍泉窯的斗笠杯,日本的刻繪四君子鐵茶託……目光再往下,木桌上老辣的包漿,紋路自然拙美,你不禁身子後仰,喲,是一張圓包圓老畫案!
目光之所及皆非俗物,主人是個講究人兒。
造一個境
·TUI CANG·
“講究人兒”林深我第一回見,但他的畫我是見過多次的:山水,松竹,一個總是身著紅袍的小人……
他的畫好認,掃一眼就知道出自他手。
他的山線喜歡自帶一條光邊,這是陽光落在物體上留下的痕跡;他的水是“牛毛”所構,“牛毛”密則水急,緩則水悠;他的松形態各異,然皆鬆散有度;其間人物,或泛舟湖上,或松下聽泉,十分瀟灑。
“先畫松樹,像一個園子造境,先植松,然後配石布水。”說起來簡單,像小孩子捏泥巴做城堡,但怎麼將松畫神,把石畫雅,把水畫活?大自然鬼斧神工,他選擇先“入山入世”。
畫武夷山,他摒去人人都畫的大王峰、玉女峰,切入武夷山的茶文化,在山裡一待五六年;畫廊橋,一整套書買回來,收集各式各樣的廊橋。
他不寫生只采風,感受四時之中自然的變幻,將走過的、見過的風景存於胸中。
然而自然之景總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他便將所見拆解,然後移花接木,將不同元素恰到好處地放到適合的位置。
是以,他的松、石、山水,美得不突兀,似乎本就該在生長在那兒。而那個小紅人,或泛舟或煮茶,怡然愜意,絲毫不覺身於畫中。
這小紅人其實是他自己,他希望造一個境,能讓自己和觀者有代入感,讓這個境“可游、可居、可望”,不嫌寡淡或喧鬧。
觀照自己
·TUI CANG·
除了必要的出行,林深大部分的時間都深居畫室。
入室一張茶桌,這是待客的地方,早年間時常彙聚茶界大師在這品茶、論茶,現在幾乎只供同道好友清談之用;兩張蘇作玫瑰椅線條流暢,做工精細,氣韻生動;左手牆上兩個櫃子裡陳列著40多把紫砂壺,這是精簡之後留下的精品。
入室右拐,左邊是日常讀書之所,右邊一整套50年代英國的老音響。這是林深花了四年多的時間從各地收回來的,連線都用的是1958年生產的美國西電老線。
再往裡,擱一張印度大葉紫檀大料所制的王世襄同款大畫案,上面置放著日本的脫胎漆盒、各色宋硯,一盤清代墨條,湖田的折腰盤……
這是他日常作畫的地方,旁人拿來當收藏品的古代文房,到他這裡基本是日用器。背後玻璃櫃打開,唐代的銅鎏板凳佛,明代的老擦擦,手臂長的沉香像飛天一樣舒展自己,吳簡木櫝,日本皇室珍藏版鐵壺……讓人眼花繚亂。
他指了指近前兩塊一米多的雙面刻漢磚,“你摸的時候會感歎古人造物的溫度。”
這些東西,在往後的日子裡讓他發現更多驚喜,在某一個特定的時候甚至又印證自己。人與物在這個空間不斷對話交流,“我不斷反觀自己,且行且悟。”
林深說話的時候泡茶的手不停,眉眼微抬,邏輯明確,是個極通透的人,更善於抓住事物的本質,多了一份從容。這份通透更讓他善於從各種事物中觀照自己。
敬畏傳統
·TUI CANG·
再回到茶桌上時,茶已經涼了。
但老音響才剛剛熱起來,蔡琴的嗓音越發沉穩有質感。西頭的窗子透進光落在內室的沙發上。遠遠的,我一邊喝茶一邊惦記沙發後面滿滿兩櫃子的書,和外頭一整櫃的《故宮文物月刊》。
乾隆曾提御筆於養心殿,“人心惟危,在閑其邪;道心惟微,在培其芽;其閑其培,皆所為養。”人心道心都得靠養,更別說古人雅意。古人經典,亦是林深日常滋養的一部分。
他的恩師林海鐘先生每次來福州,一定到他這喝茶,重題“淵淵堂”。淵,淵博,亦是“深”也,先生希望他學問要深,學識要淵博。
林深不是個保守的人,收東西只看好壞,不看新舊,但在經典上,他寧可研習傳統,因為那是經過幾千年歲月印證過的東西。
“我們為什麼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先學習傳統,先靠上去,再有自己的想法,那時候的想法才是有意義的。”經典讓他知道什麼是優什麼是劣,然後沿著這條標準線去補自己的缺陷。
為了能接古人文脈,他作畫用的是清代的墨、明代的硯臺和珍藏20多年的老紙;又買來各色的礦石磨成粉製成顏料作畫,光是拍賣中所得的精品礦料就有26公斤,不少顏色不用調配就能和古畫對上號。
他將自己畫成畫中著紅袍的小紅人,希望每天都如古人一般在山水中草堂飲茶逍遙臥遊。
“敬畏之心一定要有。為什麼要習古,是讓敬畏心有一個更深的瞭解。為什麼敬畏,不是因為古物老,是因為古物夠精彩、夠好。”
此刻的林深或許正如他所說,“有時候我會坐在各個角落,感受下空間,感受每個時刻的變化。”同畫一樣,他希望他的空間也能讓人可游、可居、可望,盡可能追求完美,不將就,不湊合。
這是他最接近古人的時刻。
文字|鄭三觀
攝影|程世達
編輯|程 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