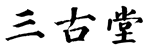那還是年前的一天夜裡。
我們一行人在山下吃完晚餐回到山裡。那會兒不到八點的樣子,近乎全圓的大月亮掛在樹梢,近得伸手就能摘到,張嘴就能吞進肚裡。
天已經黑了,但遠處的山線隱隱約約能看得見,再近一點是雲影,然後一排光禿禿的梅樹枝,最後是樹下的一池子魚。
山上的夜晚是詩意的
同行的一位老朋友,難得不顧形象地坐在庭前的臺階上,把鞋子一蹬,燃起一根煙,不說話,眼睛亮亮地沉默起來。我早在進院子前就蹬掉了拖鞋,此時坐在他邊上,煙霧下儘管他的眼睛依然有神得很,但臉部表情卻十分鬆弛。
晚餐幾杯茅臺讓大家都微醺了,微醺的大家讓院子也跟著微醺。月亮是晃蕩的,梅枝是搖擺的,池水是流動的。
月下的我們
看月亮的看月亮,拍月亮的拍月亮。
只有還算清醒的主人從屋裡搬出來茶器,在樹下的石桌上擺弄開來。沒有人管用什麼器喝什麼茶,在這樣的月色裡就很知足。
山上四季皆景
我們這群人裡,有媒體人有茶人,有研究工藝美術的,也有從事這行的,有手藝人,也有藝術家。在山下各自的好幾張臉孔,但這個夜晚,大家都褪去了社會屬性,裸露出最真實的自己。
此後的好幾次,每當我沿著山路到這裡,都會想起這個夜晚。所有發生在晚上的美好的回憶裡,總是自己做主把那天的月色替換成大臉盤。
“萬物有靈且美”
說來不是巧合,每次相約的山上的都是這夥人,頂多少一個或者多一個。這夥人年齡包含了70-90年代,在相聚在山裡之前,毫無交情可論。但大約互相看得舒服,又因主人組局,漸漸形成群體。
主人玩石刻,喜好文人生活,於是多年前將家搬進山裡。
造了園子,養了貓狗,種了梅花,挖了池子,養了肥魚。刻石的閒暇,大多時間交待給了這個園子。到最後倒成了我們的“據點”——煩惱都是他的,我們無端撿了大自在。
因總是組局提供吃喝,我們戲稱主人為“老闆”。同樣時常在局裡忙碌的女主人“老闆娘”,一頭大波浪自然卷,用她的一手好廚藝為我們端出一道道茶點和吃食。剩下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個人,除了同住山上制瓷的好鄰居時刻拖家帶口大撒狗糧外,全是貢獻大肚皮蹭吃蹭喝的,頂多再提供點尚且過得去的美照。
每次上山都帶上大肚皮蹭吃蹭喝
春天裡摘了青梅釀酒;夏天樓上樓下追著晚霞跑;秋天看山霧和楓葉;冬天煮茶賞梅花;白天喂魚玩狗;夜裡擼貓逗鳥。
夫妻倆近來熱衷燒烤,這下我們又多增加了不少樂趣:大爐子烤肉,小爐子烤蝦,提著一瓶精釀滿院子溜達;青皮羊肉好吃到爆炸,雞翅外焦裡嫩一人能啃掉一盤;天色晚了,燒烤攤捨不得收,老闆把剩餘的木炭堆進火盆,搬出庫存的土豆紅薯窩進炭裡,好茶兩泡消化肚裡庫存,晚上九點正好一人半隻紅薯,吃飽了下山。
夜茶與烤地瓜
老闆愛折騰,今天搗騰松樹,明天搗騰蒲草,一年到頭忙個不停。去年他在溪對面順流掛了幾盞燈,聽說這樣夜裡也能看到對面的山景。
有一回晚上我站在簷下往對面樹林看了幾眼,沒覺得對面有什麼景,但有種“這都是朕打下的天下”的豪情萬丈——大概境界不夠不能從對面的樹影裡看到自我和本我。夜裡有點涼,我裹緊風衣穿著拖鞋咜咜往屋裡躲。
不知什麼原因,每每到了山上,我就喜歡脫鞋脫襪,有時連中午下山吃飯也直接一雙拖鞋走天下。不聊天時光腳踩在木地板上,聊天時得摩挲著老木桌。後來老闆翻出一塊年輕時撿來的扁圓石頭放在桌上當蓋置,我就改了摩挲老木桌的習慣改成揉石頭。
擼貓逗狗喂魚,是每次上山的樂事
一樓的茶室大,光布得也好,白天簾子往下拉,晚上點了幽幽的燈,氛圍極佳。我時常喝了兩口酒就盤腿坐在地板上。有一天老闆從箱底翻出來一張牛皮鋪在地上,坐在上面柔軟舒服自在。
後來這張牛皮被挪到了院子角落的玻璃茶室裡,坐在上面視野開闊得很。
鋪著牛皮毯子的玻璃茶室
山上的我們和山下的我們好像不大相同,某些屬性暫且脫離了本體。在山下想要很多,但在山上一碗面就夠了。山林那麼大,一個院子也能待上一下午。
或許知足了才鬆弛,鬆弛了也就知足了。
鄭三觀右與退藏主理人程香左在山上
夜晚的山林安靜了,摸摸肚皮,該下山了。下山的路不長,但總覺得有個大滿月追在車後頭。路燈打在落滿雨水的車窗上分成無數光圈,積蓄好能量鼓足了勁兒準備迎接新一天的到來。
山下的我們,平庸忙碌的日子又開始了。
文字|鄭三觀
攝影|葉泓、程香、三觀、煤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