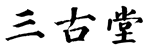陶溪川的工業革命博物館留有一張地契,這張地契代表著一個作為嫁妝的私人瓷器作坊,在五六十年代被正式歸為國營。
“
窯主的脾氣/
生於80年代的景德鎮本地人於君,回憶起孩童時期整個景德鎮的生活節奏,是步調一致的“上工”和“下工”。十多年後國營改制,數萬人踏出國營瓷廠各奔東西。
機會來了。
景德鎮陶瓷工業遺產博物館
景德鎮禦窯廠一帶
十大瓷廠統稱,實際有14家重新分割,各奔東西的人們裡頭腦活絡的小部分人紛紛承包瓷廠,成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上世紀九十年代,正是市場經濟的活躍期,作為全國唯一的手工業城市,憑藉著“千年瓷都”對國人的巨大吸引力,景德鎮在內部“解放”的同時,也招來了不少外來資本。
這兩撥佼佼者組成了這個城市的第一波“窯主”,而邁出國營大門的其他匠人窯工也被正式宣告沒了鐵飯碗。他們自找出路,畫畫的、燒窯的、拉坯的、修坯的、築模的、煉泥的……大部分的工人匠人紛紛在新的私人瓷廠裡找到了相應的位置。這個城市似乎又恢復了往日“上工下工”的號角。
但景德鎮的窯主並不好當。
燒廢的瓷片
把名字落在瓷器上
除了本錢和膽子,你還得熟知制瓷流程,否則管理很難有標準。從90年代中到21世紀初,景德鎮來來往往的企業家一批接著一批被淘汰,這個大浪淘沙的過程一直持續到新世紀才算堪堪穩住。
銘清堂主理人 於君
“當窯主太累了。”於君笑著說道。
他四十多歲,這幾年的窯主日子讓他兩鬢生了白髮。若按正經劃分,他得歸為第二批自主創業的私人窯主。他的老東家,是景德鎮的一線窯口“春風祥玉”。
于君作品以畫工見長
從一個畫師到獨立運營一個窯口,於君可謂過五關斬六將。得找泥料供應商、得找拉坯師傅修坯師傅、早期得找合適的窯爐“搭窯”,還得從單純的畫畫直面市場經濟的殘酷。
於君的“銘清堂”成立於2016年,它以畫工見長。作窯主之後,於君每天還依然堅持畫超過八小時,他心裡清楚地知道,他的買家看上的是他個人,是“於君”這個名字。所以,除了個別的“年末福利”外,於君的每個杯子幾乎都只出現30個或50個,哪怕再完美,第31或者第51個杯子也只能藏於家中,不賣不贈。
不該掙的錢堅決不掙,憑著對自己的高要求,銘清堂的器皿在玩家手中價格越炒越高。儘管他所掙不多,但玩家認同器皿的升值空間讓他一點不缺成就感。
儘管困難重重,於君還是守著自己的“臭脾氣”硬生生扛住了。
像他這樣從瓷廠獨立成立小“作坊”的窯主不在少數,再加上外來資本和本地瓷器愛好者的投注,在不斷的淘洗中,景德鎮形成了百花齊放的“窯主文化”。他們中有些以柴窯為代表,有些以畫工取勝,有些因極具辨識度的瓷器風格獲得買家認同,不同的路子,但相同的是對陶瓷品質的追求。
妙色青花主理人 老張
三年投入400萬被柴窯“耽誤”的妙色老張
“妙色青花”的老張2015年開始投入柴窯燒制,他找了一座十幾年的老柴窯,在砸入接近400萬後才成功燒制出第一窯瓷器。作為景德鎮外來人口,又不是瓷器從業者,這個“窯主”他做得萬分辛苦。但柴窯青花猶如豬油一樣帶著呼吸的溫潤和仿佛泥胎中生長出來的青花,還是吸引著他一天天堅持下來。
好在同樣追求柴窯質感的人少但依然存在,妙色青花在挨過寒冬後在市場立足,窯廠逐漸穩定下來。
穩定後的老張開始放飛自己,試色試型,從前開窯時那種慌張感早就丟得差不多,現在好像更多是一種“玩”的狀態——管他賣得好不好,先燒得高興再說。
克勤堂以高度復原元青花聞名遐邇
景德鎮是個包羅萬象的地方,也是傳統和當代碰撞的地方。
這裡既有像“克勤堂”這樣極致的元青花復原者,也有像王波這樣的藝術青年。
王波是藝術圈的叛逃者,他在海市蜃樓般的藝術夢破滅後著手汝瓷燒制。從純西式的藝術範疇到中式審美,180度的轉變讓他游離在藝術圈和制瓷人之間。但瓷器讓他真正接受了自我,從一灘爛泥到一個絢麗的杯子,這個過程的反復重複讓他一次次確立了自己的信心。
藝術圈的叛逃者 王波
在和世界和解後,王波變得平和從容。
他開始考慮把手上的泥作為表達的素材。情緒、觀念、想法可以通過繪畫和雕塑傳達,那日常的器皿又為何不能承載?他想做一隻這樣的杯子。從燒制第一窯開始,他就把所有的瑕疵品堆積在窯爐邊上。幾年下來,它們早已成為一堵厚牆,但王波始終沒有做出讓自己100%滿意的杯子。
王波在工作中
“哪天我做出這樣的杯子,我可能也就不做瓷器了,”他一邊說一邊吐出一口濃煙——看這情形,骨子裡還是藝術家脾氣。
月雲堂主理人 胡兵
“月雲堂”的胡兵在東風瓷廠改制後提著蛇皮袋到全國各地做展會“看世界”,他在麻六甲找到了對瓷器和傳統文化的發自內心的敬畏和熱愛,也為自己將瓷器作為謀生工具感到羞愧。
而立之年後,他從國外落葉歸根回到景德鎮,先是經營古陶瓷研究所,後創立仿古瓷品牌“月雲堂”。從五千年的華夏文化中找尋符合當代審美和需求的元素,將自己遇到的心儀的古陶瓷複刻出來呈現在大眾眼前,這是“月雲堂”的初心。
因為見識廣泛,“月雲堂”不像其他窯口專做一門,而是漫步于單色釉、青花瓷、琺瑯彩粉彩等各種瓷器門類了。未來怎樣不好說,但極致的工藝和審美,是胡兵心中“雖不可及但心甚嚮往”的彼岸。
雨中的柴窯
和窯主聊天是有趣的事,他們大多故事多還極具幽默感;他們的人生經歷似乎平常但又很不平凡;他們隨著大環境的浪濤裡起起落落,但總能抓住水面的浮木;他們有自己的堅守,在堅守的同時,也保持自己的“玩心”,去嘗試可能市場不接受但內心很愉悅的瓷器的可能性。
這些富有張力和意趣的一個個“個人”編織成了景德鎮的活力。而窯主對瓷器的審美取向和工藝追求也讓景德鎮的瓷器多元豐富。
柴窯的溫潤讓人難以“放手”
窯主在玩家心中是很特別的存在
窯主在玩家心中是很特別的存在,他們認人認器認限量和編號。
儘管以出手價來看,窯主們常常只能維持作坊運營,但私底下的瓷器價格經常被玩家炒到三四倍。為了這些玩家玩得“盡興”,在標準以下的成品不被允許出街,在標準以上的“編號”外的也只能藏在家裡。
這就好比你握著沙子,手松一松錢就來了,但你非但不能送,還得握得更緊——窯主們都知道,握緊後出的沙子更細更綿長。
自由生長或許是當下景德鎮柴窯最好的發展模式
景德鎮窯主文化從開始到現在不過30年,儘管還有許多不足,但他們讓我想起了明清時期那些極具魄力的商號,也讓我想起了日本那些百年傳承的堂號。
逐漸生長的東西誰也說不準盡頭在哪裡。但想想幾百年後有人從地下挖出各大窯口的瓷器,他們是否也會感歎到這個時代中國瓷器的百花齊放和精妙工藝呢?
而現在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放任窯主們的脾氣,讓他們自由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