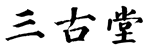林建軍
1979年生,
國家級非遺莆田木雕代表性傳承人
藏雲堂藝術雕刻品牌創始人
在見過林建軍後的很多天,一個場景在我腦海裡反復出現:
40多度高溫裡,切割成一公畝大小的鹽田一塊塊相連。年幼的林建軍送完飯後,他和父親踩在黑色的土地上,一人一邊拉著繩子,用人力重複不斷地攪動池裡的鹽以防止結晶粗大。這種在現代我們觸碰不到的生存狀態,被林建軍稱之為“一個平常的日子”。
二十多年後,林建軍刻了一組雪山大士。這個題材在佛教中代表釋迦摩尼雪山苦行的形象。
精微透雕雪山大士
他從十幾公分刻到不可思議的五毫米,一次次挑戰自己的極限。這時他早已不是當初那個瘦小的十歲孩童,但穿越時空的兩個身影卻在我腦子裡逐漸重疊——不斷從舒適圈走出來,在艱難的環境裡咬牙堅持,並不斷重複這個過程。
這是林建軍修行的方式。
01
/
入海
16歲那年,林建軍從莆田老家乘車到福州做壽山石雕學徒,一路上看著窗外景色的變化,他精神飽滿地憧憬美好的未來。到了作坊一看,兩排大通鋪,機子一動整個工作間都是白灰,每個人都灰頭土臉。連口罩都沒有防護。兩個多月後家人來看望他,用了“再待下去會死掉”來形容那時的生存環境,硬把他帶回老家。
儘管如此,在16歲之前,在那個缺乏精神食糧也沒有努力方向的農村生活裡,這個短暫的學藝機會對他來說彌足珍貴,“學徒很辛苦,但是我很快樂。”
快樂的源頭在於每天都有新的東西填充進白紙裡,就像一隻擁有無限記憶體的海綿渡過了十萬八千里沙漠後入了海,瞬間充實飽滿。
工作中的林建軍
從此,“往裡收東西”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無論是石雕還是後續轉學木雕,當同廠的年輕人還沉浸在歌舞廳時,他躲在樓頂就著20瓦的燈泡學打坯;當大部分人還在為自己的一點手藝沾沾自喜時,他已經暗戳戳想學好每道流程自己創業。
從一個初出茅廬的學徒到成為廠裡獨當一面的木雕師傅,他花了將近十年時間。
十年後,他的人生開了掛。但是,“往裡收東西”這個習慣卻從沒放下過。
02
/
人設
時間輾轉到2003年,在那個木雕生意好做得不得了的年代,林建軍看到了產品同質化帶來的危機。
他在上海見過橄欖核雕,小小一隻橄欖核,卻能刻畫《核舟記》那段經典畫面;也在福州看過大量的壽山石雕,薄藝、巧色等技法的應用讓壽山石雕快速崛起。莆田木雕有什麼呢?他想到了一句老話——莆田木雕素以精微透雕聞名。
但是精微透雕在哪兒呢?沒有人知道。
林建軍精微透雕工作室
在幾乎人人都因為難度太高而放棄時,林建軍決定舉起這帆大旗。他不知道市場在哪兒,但是他知道這是“有意義的事”。花了兩年時間,林建軍工作室在傳統透雕、圓雕、高浮雕、淺浮雕等工藝基礎上,融合兄弟藝術竹刻、壽山石、玉雕等手法,重新梳理出精微透雕的技藝。精微透雕一經面世,先引來了識貨的同行們。
精微透雕不同於一般的莆田木雕,除了用料挑剔之外,它對材料的捨棄更多。更重要的是它對技法的要求決定了週期不會短。從選材到被買家收藏,前後需歷經數年,甚至十多年。
這種不同以往“雕了賣,賣了雕”的創作方式徹底磨練了一個人的心性。撇開浮華和躁動,他把對雕刻的理解和生活的感悟都放在作品裡,“你要往裡注入精氣神”。
藏雲堂內景
自打和精微透雕綁在一起後,林建軍便被打上了“工藝大師”和“傳承人”的標籤。出現在大眾視野裡的林建軍大多消瘦、嚴謹,標配是黑框眼鏡、白襯衫,行走間自帶清風。
但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深色無袖運動衫、短褲、一雙拖鞋,偏白的膚色,面龐清秀,眉眼乾淨,就像剛打完一場球賽回家的大學生。
“我要重構我的藝術人設。”他一邊說著這話,一邊把玩著手裡的一塊根瘤,佈滿瘤紋的木頭像人的腦瓜子。
03
/
重構
這是他最近找到的一個準備拿來創作的料子。
原先他想在“腦瓜子”上插一些電線和USB,沒過幾小時他又覺得這個想法太俗,一點都不酷,乾脆捨棄。他把這個料子放在茶桌上,沒事的時候摸一摸玩一玩,它的形象也從“腦瓜子”拓展成月球表面和龜背。
事實上,“重構藝術人設”這個說法並不準確,如果你認真看過他的作品,同他聊過天就會知道,他的人設不應該只有“勵志”和“傳承”。
他的作品“羿射九日”在保留木頭本身疤紋的基礎上,結合了壽山石巧色工藝,將疤痕化為太陽,這不僅是技藝的創新,更是一種雕刻觀念的轉變;同樣別出心裁的作品還有2004年的“如花”,原料來自柴火堆。林建軍看中了它“性感”的紋路,當時還在雕佛像的他順應木頭紋理將它雕琢出一張少女背影來,畫面乾淨清澈。
羿射九日-林建軍作品
如花-林建軍作品
這是一種純自然的“撓癢”式表達,簡單來說,就是看到了、心癢了,那就去表達。這種天生的覺知能力不禁讓我產生一個疑問,精微透雕真的成就了林建軍嗎?如果沒有一頭紮進精微透雕這種複雜的工藝裡,他會不會成為一個比較“當代”的藝術家林建軍?
林建軍工作室的角落裡藏著一個特別的作品,它的“頭”高高昂起,“四肢”像依然活著的、不斷向四面生長的老樹根。林建軍保留了原木的所有造型,唯獨在頭部幾筆刻出龍頭和鬃毛,“在扭曲中掙扎,依然高高昂起頭顱,這不就是中國人的龍馬精神’?”
龍馬精神-林建軍作品
五百羅漢-林建軍作品
木供石-林建軍作品
很顯然,精微透雕並沒有抹去他的覺知力,反而讓他在沉澱後的創作顯得內斂且富有張力。他的覺知力隱藏在遵從時間和自然痕跡的“木供石”系列裡,也隱藏在讓你仿若置身山中尋找千佛窟的“500羅漢”裡。
04
/
覺醒
林建軍在這一兩年的變化很大。
原來的他是一個把時間規劃得一絲不苟的“趕路人”,現在的他會在後院種葫蘆,會關心外面的棗樹開花沒有,也會把時間“浪費”在哲學和詩歌裡。
因為疫情,持續半年的中場休息中,林建軍創作了“命運共同體”。五種顏色的口罩代表五大洲,它們緊密相連,寓意五大洲人民攜手抗疫,戰勝新冠疫情。如果說“如花”和“羿射九日”是他自然而然的情感抒發,那這件作品就是時隔16年後有意識地自我表達。
命運共同體-林建軍作品
他把自己稱作“在藝術上很善變的人”,從對一切審美都充滿好奇,到不斷探索技藝的終點,再到化繁為簡回歸內心,他一直在不斷塑造藝術人設、打破藝術人設、重塑藝術人設。
但當我看著這個不惑之年的工藝大師在山裡牽著妻子的手,光腳坐在石頭上踩著溪水玩時,我突然明白,這不是“善變”,而是“解放”和“覺醒”。
林建軍和太太
從學徒到師傅再到工藝大師,他的雕刻生涯已走了26年,為了生存、為了傳承、為了養家糊口的日子已經過去,他正在從一個手藝人的身份回歸到了自我的本真。
他的本真是什麼呢?就是天然感知力的全然覺醒和解放天性式的獨立思考。
中國人常說,四十不惑,“不惑僅僅只是不迷惑嗎?你還要找到方向,這個方向就是從表達美’轉向表達觀念’”,從前不擅表達的林建軍,到今天能夠自如地說出心底想說的話:“就像古人說和光同塵’,我們不是光’,只是塵’,普通人要在歷史中留下點東西,一定是去表達他的唯一性。”
這是他認為的一個人應該有的社會責任感,也是當代手藝人應該有的“覺醒”。
藏雲堂內景
一天的採訪下來,太陽漸漸下山,夫妻倆在門口的棗樹下送別我們。路邊幾隻野狗還在搶奪陳琴投喂的食物,朦朦朧朧的霞光打在他們身上,程香對我說了句,“他們倆真是少有的氣質乾淨的人。”
但我的注意力還放在那叫做《龍馬精神》的作品裡,“在扭曲掙扎中依然高昂著頭”,這說的是他眼中的中國人,卻也是我們眼中的他啊:始終保持清醒,帶著一股靈氣和傲氣,充滿東方味道卻又極為“當代”,像“時刻準備要衝出去”,又像一個旁觀者看著這個世界的喜樂和荒誕。
木供石系列——林建軍作品
這是當代手藝人的“覺醒”,也是四十二歲林建軍的“覺醒”。
文字|鄭三觀
攝影|藏雲堂、程香、鄭三觀